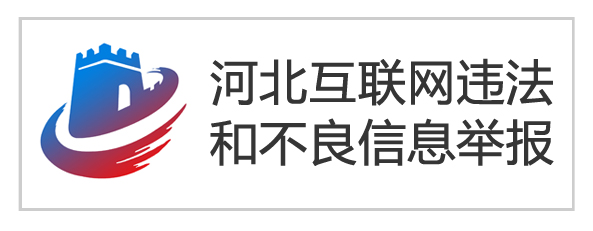□ 刘兰根
小时候的老家农村,家家吃饭用的都是粗瓷碗,有比普通碗大一号的,称为“二碗儿”,还有更大一号的,称为“白碗儿”。那时候的人干活卖力气,饭量都大,再加上饭菜里没什么油水,所以一人每顿吃两三碗饭很正常。
我有个同族叔叔,排行老四,每顿都能吃四碗饭,乡邻们都喊他“四大碗儿”。有时干打坯盖房或下河挖渠的力气活,人们就会有滋有味地谈论起谁吃得最多,吃四五个白面卷子不算稀罕,据说村里有一人一顿吃了一胳膊卷子,人们都纳闷这一胳膊是多少,原来是这个人把左胳膊伸直,把卷子一个个横着排起,直到手心,具体多少个记不清了,反正右手一个个地拿起吃,没多长时间,全部吃完了,让人们大开眼界。
那时候打井挖渠的壮劳力在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吃饭,比家里的饭要好很多,家里不常见的白面卷子这里有,甚至还有肉馅包子。有一个伙夫爱贪小便宜,经常克扣大家的口粮,做的肉馅包子其实只是在菜馅里放了很少的肉,大家经常会挨饿。有一次,一个壮劳力发现了端倪,在包子刚掀开锅时,趁伙夫去墙边放锅盖,专门从锅边挑了几个包子放到自己的碗里,坐在一块砖头上吃起来。他吃得又香又饱,吃完后故意冲着伙夫大声说着风凉话:“这是谁蒸的包子啊,还往里掺麦秸,想卡死我啊。”伙夫涨红了脸不说话。原来,这是伙夫专门蒸了几个放肉多的包子留下给自己吃,为做记号,就在每个包子的捏口处放了一小截麦秸,没想到被壮劳力发现了秘密。
那时候家家吃饭都是在地上的小饭桌上,坐小板凳,有的男人爱端着饭碗到墙根底下蹲着吃。冬天一般把饭桌放到土炕上,土炕下连着堂屋烧柴的灶火,很暖和,家庭主妇一般坐在炕沿,负责给一家人盛饭,一顿饭下来要来来回回好多趟。如有客人吃饭,会被让进炕里坐,这是最高的礼遇。给客人让饭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,客人吃一碗饭肯定不够,主妇就会接过碗来添饭,客人还要客气一下:“不吃了不吃了,够了够了。”这边就要劝饭:“再吃点儿再吃点儿。”在客人的半推半就中,又盛满了一碗。那一次,我住在姥娘家,姥娘给客人让饭,客人吃完一碗饭后连说:“不吃了不吃了,真饱了。”姥娘热情,非得夺碗添饭,客人就往回夺碗,夺来夺去,一个有裂纹的粗瓷碗竟然被夺成了两半儿。
那时候只有县城才有一个大点的饭馆儿,称为“食堂”,父亲曾在夏天带我去吃过一次麻酱捞面,屋顶上竟然有电风扇快速转动,我特别好奇,因为那时我们村里还没有通电。捞面特别香,电风扇也特别凉爽,我舍不得大口把面吃掉,一小根一小根地慢慢嘬,还不时抬头看一眼转动的电风扇。那顿饭我吃了很长时间,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。
家里的主食以玉米面窝头为主,有时候还会掺高粱面。我不喜欢吃这样的窝头,但是除非逢年过节,母亲很少蒸白面卷子。村里出现卷子房后,好多人用麦子去换卷子,换卷子的也在每天傍晚走街串巷。有一次,月亮升起来的时候,我们才在院子里的小饭桌上吃饭,放了好几天的窝头干巴了,硬中还有酸味,实在不好下咽,我央求母亲去换几个卷子吃,母亲舍不得麦子,坚决不同意,说:“不年不节的,吃什么卷子!”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,母亲叹了口气,拿一只小搪瓷缸从厢房里装了一小缸麦子,对我说:“要不你去二铁头的卷子房换一个卷子吧,你自己吃,我们可不吃。”我看了看那一小缸麦子,摇摇头说不吃了,因为这些麦子实在是太少了,仅够换一个卷子的,来回要走三里地,吃下一个卷子,还会落下一个嘴馋的名声,我还是忍住饥饿睡觉去了。
如今四十多年过去,各种菜品应有尽有,不但超市里的货品琳琅满目,还可以邮购外地的特色食品,街上的饭馆到处都是,如果叫外卖,不到半小时就可以送饭上门。但我总是喜欢自己动手,那种与粮食的亲密接触,那种粮食的香甜味道,常常让我漾起幸福的满足感。那些年那些关于吃的故事,也常常会涌上心头。
(作者单位: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检察院)



 上一版
上一版